作者:温故
编辑:白鱼
作者有话说:
舒蕴爱阿若吗?可能有人看到最后,会有这么一个问题。
我来替他回答一下。他爱的,可在这份爱之前,又事关着两个国家的命运。
就像阿若曾说过,学中原话是为了占领中原一样,就算舒蕴没有做那些事情,他们也终将成为敌对面。
从相遇开始,他们的命运便早已决定。
一
隆冬,大地银装素裹。南至大泽川,北至不句山脉,皆是一片素白。
大楚和亲的公主长宁便是这个时候来的白氏国。随长宁一起到白氏的,除了数里红妆,几百奴仆,还有前来为质的镇国大将军之子——舒蕴。
父汗嘱咐丹溪要好好盯紧他,只是阿若看着舒蕴苍白的样子,对父汗的话嗤之以鼻。这般病恹恹的模样,还能翻了天?想必丹溪也是这般认为的,所以,这个任务最后被他踢到了阿若的头上。
只是阿若也是不服管的,她是白氏的公主,也没人敢拘着她。等她去不句山打了几日猎,回来时路过阿塔木湖,瞧见那安静垂钓的身影,才想起丹溪交代她的话。
彼时风雪不停,阿若翻身下马,坐到他身边,看着鱼线没入结了冰的湖中,嗤笑一声:“你这样是没有用的。”
舒蕴的脸埋在蓑衣中,肩上堆了一层薄雪,说:“无碍,只是喜欢此间意境。”
阿若撇撇嘴:“说什么呢?文绉绉的……”
雪越发大了,像大团大团的棉花,偶有几片落入衣领中化成了水,顺着脖子流了下去。阿若揉了揉鼻子,张嘴就是一个喷嚏。等喷嚏打完,头顶便多了一顶斗笠,暖热了小姑娘冻得通红的耳朵。
阿若握住斗笠的边缘,并没有第一时间将它摘下来,却也不肯在这中原人面前示弱:“我不冷。”
舒蕴神色泰然:“我知道,是我热了而已。”
阿若侧头觑了觑他,好一会儿,才不情不愿地嘀咕:“那好吧。”
活似委屈了她一样。
舒蕴见阿若脸上秀气的眉毛蹙成一团,不由得失笑:“公主中原话说得很好。”
阿若顿时又眉飞色舞起来:“那是,我们白氏以后可是要统治中原的,自然得会说中原话!”
舒蕴仍是笑,他看着阿若,只摇头道: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阿若便不高兴了。她想一脚将舒蕴踹到湖里,只是见他羸弱不堪的模样,觉得自己这一脚下去,他可能就没命了,便掬了一捧雪,迅速塞进舒蕴的衣领中。
舒蕴就此病了大半个月。
再见到他是在那达慕大会上。丹溪说这次大会选出的第一勇士,未来也许会成为阿若的夫君。
丹溪一向是没个正形的,哄着阿若,非让她在一众打赤膊的儿郎中选出个心悦的来。阿若也不臊,眼神一扫,便看到了人群中的舒蕴。
丹溪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,笑话她:“长得是好,可就这身子,挨不挨得过冬天都不一定。你说呢?”
阿若想起在阿塔木湖遇见舒蕴时他说的那些话,不由得鼓起腮帮子,恨恨地说道:“对,不能!”
二
在白氏,但凡不下雪的天气便是好天气。
前两日,丹溪拘着阿若不让她出去,早将她闷坏了。这日一放晴,阿若便牵了马,打算去不句山打猎。路过舒蕴的帐篷时,正好碰见舒蕴掀帘出来。
那日那达慕大会举行到一半,风雪大了起来,裹得极为厚实的舒蕴据说又受了风寒。
阿若想到此处,按辔垂眸看他,惊讶地问道:“你今日竟出来了?”
舒蕴抿唇冲着阿若笑了笑:“公主雅兴。”
阿若一向最腻味中原人说话文绉绉,于是一扬鞭,抽得马儿嘶鸣着一脚踏在舒蕴身边,溅了他一身雪才满意。
舒蕴伸手将那些碎雪拂落,也不恼:“雪路难行,公主当心些。”
阿若皱眉,骑马绕着舒蕴走了一圈,问:“中原人都跟你一样虚伪吗?”
明明就不想理她,还非得装出一副温柔可亲的模样。
舒蕴缓声道:“反正中原是没有公主这般的姑娘的。”
“听说中原的姑娘个个娇弱无力,我才不要像她们!”阿若“哼”了一声,眉眼凌厉张扬,“喂,病秧子,我们要不要比一比?”
舒蕴抬首看着阿若,许久才道:“公主想比什么?”
“打猎!”
此前连日的大雪已将不句山所有的路封埋,马儿涉雪走得很是艰难,后面阿若干脆弃马,背着箭囊自己下来走。
舒蕴见状,便也下了马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阿若身后。
阿若看着舒蕴苍白似雪的脸色,撇撇嘴:“你可别死在这里了。”
舒蕴抿着唇没说话。
阿若见他苍白的脸上多了几分坚毅,心猛地一跳。她忙不迭移开视线,却无意瞥到舒蕴脚上那双湿透了的缎面靴,不由得皱眉道:“在白氏,大家都是穿小鹿皮靴子,你没有?”
转念又想到舒蕴他们初到白氏时,丹溪兴致勃勃地分发给他部下的那些鹿皮靴,阿若便有些说不出话来了。
只是看着舒蕴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,阿若又禁不住有些气恼。她扬鞭往一旁的树上狠狠一抽,趁着积雪簌簌洒落,将两人的视线隔开时,极快地用白氏语说了一句话。
纷扬落下的白雪中,舒蕴愣了愣,下一刻便朝阿若扑过来:“小心!”
阿若被舒蕴护在怀中,两人相拥着在雪地里滚了好几圈,等停下来时,雪地上已经洇开了一长串血迹。
有狼!
三
舒蕴是在午夜时分醒来的。
外面似乎又下起了雪,扑扑簌簌。舒蕴看着帐顶,几乎可以听到雪花落在毡帐顶上的声音。
他想起身,只是稍一动,伤处的疼痛便让他闷哼了一声。正要躺回去时,黑暗中却有个身影摇晃着站了起来。
阿若揉着眼睛,将毡帐内的烛台点亮,迷迷糊糊地问舒蕴:“怎么了?”
舒蕴有些惊诧,他像是没料到阿若会在这里守着他,好一会儿才哑着嗓子道:“公主在啊?”
“我怕你死了啊。”阿若嘟嘟囔囔,又往他的床头一趴,打着哈欠道,“你不能死掉……”
舒蕴本来倾身凝神听她说话,结果一句话说罢,这小姑娘半晌没了动静,只有那花花绿绿的辫子散落在床榻,一半压在了舒蕴的手背上。
他看了一会儿,本想抽回,不想那睡得人事不知的姑娘得寸进尺,脑袋一挪竟是直接将脸凑到了他掌心。他有些愣怔,许久,却是慢慢弯起了唇……
舒蕴这一养伤便养到了暮冬。积雪逐渐消融,融融一点绿意露了出来。白氏的春天快要来了。
阿若是闲不住的,成日跑来跑去,一会儿去不句山摘了几朵花,一会儿又去阿塔木湖捕了几尾鱼,献宝似的捧到舒蕴跟前,问:“你喜不喜欢?”
舒蕴总是先道句“喜欢”后再教导她:“这时节最容易遇上蛇虫猛兽了,公主还是别乱跑。”
阿若偷偷觑了一眼舒蕴,竟难得地受教,乖乖挨着他坐下:“其实当时你不用帮我挡的。”
当时在不句山遇狼,舒蕴帮阿若挡了两次,一次伤在肩胛,一次伤在腰腹。
舒蕴正色道:“女孩子是不能留疤的。”
“为什么不能?”阿若捋起袖子给他看,“我手上就有疤!”
那一截莹白让舒蕴难得有些窘迫,他移开视线:“公主,女孩子是不能随便露出肌肤的。”
“你们中原规矩真多!”阿若哼了一声,问,“中原的姑娘好看吗?”
舒蕴点了点头。
阿若心里便有些郁郁了,只是白氏的姑娘一向胆大,她又问:“那你有喜欢的姑娘吗?”
瞧着阿若眼中毫不掩饰的期待,舒蕴一顿,隔了一会儿才轻声说:“没有。”
阿若的眸光一瞬便亮了起来。两人此时正坐在一方小土丘上,恰逢晚夜,月色与雪色交织。阿若安静不下来,又偏头问舒蕴:“白氏和中原的月亮,谁更漂亮?”
舒蕴无奈:“公主,哪里的月亮都是一样的。”
阿若想了想:“那你干脆别回中原了。”
白氏虽比不得中原富饶,可白氏人从不会像中原人一样,把人当牲畜似的送来送去。
舒蕴默然了一瞬,而后又笑起来,问阿若:“当时在不句山,公主是不是用白氏语骂我了?”
阿若没甚心眼,舒蕴将话题这么一转,她便被带过去了,睁圆了眼睛顺着他的话道:“你听得懂白氏语?”
“之前病中无事,便学了一两句。”
阿若便像偷蜜糖被抓了现行的小耗子,整个人从土丘上蹦起来,磕磕巴巴却又嘴硬道:“我……我就……就是骂你怎么了?谁让你什么都不说,难……难怪会被丹溪欺负!”
舒蕴的眸光在月色映衬下慢慢亮起来,他轻轻笑着,说:“好,以后我什么都跟公主说。”
阿若一怔,在越发剧烈的心跳声中仓皇逃了。
四
惊蛰过后,父汗调了旗下半数的军队,分成十支,遣他们沿着不句山脉去寻找新的草场。本来丹溪也独领了一支,朝着西北方向走,结果他连鄢支山都没翻过,就嚷着冷,自个儿打马回来了。
父汗气得狠抽了他两鞭子,转头这厮就笑嘻嘻地找上了阿若。
彼时,阿若正让舒蕴教她识别草药,枝叶根茎铺了满桌,好不容易记住几样,被掀帘而入的丹溪一吓,顿时什么都忘干净了。
阿若没好气地抓了一把草药朝丹溪扔过去,骂道:“成天惦记着族中的姑娘,前儿玛雅姐姐还生了个女儿,你要?”
“那倒不必。”丹溪素来脸皮厚,裘袄一掀,挨着阿若坐下,眼睛却滴溜溜在舒蕴身上打转,“他怎么在这儿?”
他俩一直说的白氏话,也不知舒蕴听没听懂,但他大抵是看出了丹溪眼中的探寻,丹溪刚问完阿若,他便起身鞠了个礼:“先告退了。”
丹溪最烦这些繁文缛节,撑着下巴“啧”了一声,用白氏语悄悄地骂:“虚伪。”
阿若瞪了他一眼。待丹溪消停了,这才又转头看着舒蕴,不大乐意的模样:“可是这些我都还没有记住,怎么办?”
“无事,日后再学也无妨。”舒蕴温和地笑着,又作了一揖后,这才掀帘离去。
阿若便又乖乖地坐下,望着舒蕴离开的地方出了一会儿神,待想起毡帐里还有个人精丹溪时,已经晚了。
“也不是不可以。”丹溪将食指在桌上轻轻叩着,一贯上扬的嘴角慢慢展平,“可是阿若,你想过没有?他不一定会留在白氏。”
阿若不懂:“可中原人对他不好,他们将他送到了白氏。那他又何必要回去?”
丹溪叹了一口气,揉了揉她的脑袋,换上难得正经的语气,说:“倘有一日,父兄无用,须得将你送至别国他乡,你会怨我们吗?”
阿若愣了愣,垂下头,一会儿后,又觉不甘心,嘟囔道:“中原人不是一向重视子嗣吗?待我为他生个孩子,他也许就不会离开了。”
丹溪听罢,顿时一根手指狠戳上阿若的额头,咬牙骂道:“被个中原男子迷成了这般模样,你当真是出息!”
很快,丹溪便知道阿若不只是出息了,而且是出息大了。
傍晚时分,负责监视舒蕴的奴仆慌忙来禀,说人不见了。仔细一盘问,才知这奴仆怠懒,打舒蕴从阿若帐篷里出来,说要再去摘些草药后,便没再看着他,自个儿躲到马厩里睡大觉去了。
丹溪听闻,也不慌,只打着哈欠同阿若道:“瞧瞧,方才我说什么来着?”
阿若不说话,直到半个时辰后仍不见人归来,她才将马鞭一揣:“我去找一下。”
丹溪拦住她:“这天气眼见就要下雪,你现在出去,到时候人没找着,自己还回不来了。”
阿若不听,扬鞭擦着丹溪的脸一甩,趁他不备,牵了马便跑。
这时已有飞絮似的雪片落下来了,丹溪气急败坏,掀帘想追,结果眼前一片茫茫雪幕,哪里还看得见人影?
问清舒蕴是向南行以后,阿若便一直打马南奔。
一时间风雪不息,刀子似的往脸上刮,在雪中疾奔一个多时辰,隐约能透过风雪看到涿光山的全貌后,阿若这才感觉到了冷。
越过涿光山,便是回中原的路。
她将毡帽拽了拽,遮住鬓角,按辔调转了马头……
回去的速度比来时要慢上许多,也不知是马累了,还是阿若累了,一人一骑就这么缓缓地在雪地里走着。
方至亥时,路过柴达的一片戈壁滩,阿若瞥见石缝里透出一片暖融融的火光,火光中映出一张清隽熟悉的脸后,她紧绷着的心弦这才一松,在舒蕴惊讶的神色中从马背上栽了下来。
五
事后,丹溪打趣阿若:“也真是稀奇,平时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柔弱身子,竟能将你从柴达背回来。”
阿若酡红着脸,手指绞着鹿皮毛毡,犟嘴:“柴达离这里又不远。”
“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丹溪嗤笑道,“你好好给我在床上躺着,手脚都差点儿冻坏了,就别想着往别的毡帐跑了。估摸着再有几天出去寻找草场的人也会有消息传来了,到时你这腿脚不好,人又沉的,谁乐意拉着你走?那边我命人好好伺候着呢,你且放心,轻易死不了的。”
阿若一听这话便不乐意了,嘴噘得能挂个铜壶:“谁沉了!而且他现在都还昏迷着,要是醒不过来怎么办?”
丹溪耸了耸肩,一副浑不在意的模样:“那也是他命该如此。”
阿若气得直接将一个羊角枕向他扔了过去。
丹溪眼疾手快,接过羊角枕抱在怀里,又往阿若床边一坐,神色凝重起来,问:“好端端的,他怎么会走到柴达去?你可问过他没有?”
阿若心气儿还未消,瞪了丹溪一眼:“柴达那处的草木与牧场上的不一样,他说想多找几种教我分辨,结果一时走远了,回来时便遇上了风雪。”
“你信了?”
“这有什么不能信的?”阿若撇嘴,“反正我找到他的时候,他身边堆满了花草的根茎。”
丹溪“啧”了一声,揪她的辫子:“中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?女大不中留!我看你,趁早嫁了算了。”
阿若原本也想着,等舒蕴醒过来,她便去将这事禀告给父汗,父汗一向疼她,不会不答应。只是不承想,她还没开口,中原那边便递来了消息,说愿以千匹绫罗并百箱珠宝换回舒蕴。
当初父汗提出要舒家儿子为质,本意也不过是想恶心一下那位与白氏素有仇怨的镇国大将军,但如今舒蕴高热不退,昏迷不醒,挨不挨得过去都不知道,自是没什么为质的价值了。故而中原一开出条件,父汗便立即应了下来。
阿若知道消息的时候,中原那边已经派人来接了。
丹溪负责拦她,结果被她抽了一鞭子。丹溪没什么事,阿若被冻伤的手反倒皲裂开了,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。
“你现在追出去,难道他就会让你随他一起走吗?”丹溪狠了心,“阿若,你明明知道,他并没有给你任何承诺。当你心急如焚去找他的时候,他可能巴不得避开你,好联系中原人,让他们接他回家!”
“我不信,我要去找他!”话音刚落,帐篷被掀开,阿若要找的人徐徐走了进来。
舒蕴脸上还有潮红未散,说话的时候压着嗓子,将咳嗽声闷在了胸腔:“今日……特来向公主辞行。”
阿若急喘几下,流血的手指着丹溪,问舒蕴:“方才他说的话,你可听见了?”
舒蕴垂眸颔首。
阿若咬牙,又问:“他说你那日是故意跑出去联系中原人的,这话可是真的?”
“是。”有风从未合拢的帐帘缝隙钻了进来,舒蕴又压下了一声咳嗽,而后低头朝着阿若拱手,“承蒙公主连日照拂,舒蕴愧不敢当。日后还愿公主……身体康健,岁岁长欢。”
手背有疼痛感传来,阿若咽下喉间那丝呜咽,笑出声来:“好一个‘愧不敢当’。”
六
舒蕴走后两个月,长宁公主有喜。这中原来的公主是位合格的闺秀,除了三个月前阖族迁往新牧场时有过短暂的露面,其余时间基本待在自己的毡帐里。
反观阿若,打舒蕴走后,便比之前还要闹腾。一会儿偷了人家的小羊羔子,一会儿又撵着马群四处跑,像是压根儿没把之前那场失败的情窦初开放在心上。这可苦了白氏的牧民们,既不敢打,也不敢骂,只有偷偷向可汗告状。
告状的人多了,便也成了气候。舒蕴离开的第五个月,白氏水草最鲜嫩,猎物最肥美的时候,阿若被关了禁闭。
说是关禁闭,其实也只是让阿若搬进长宁公主的帐篷,责令她随这位中原公主好好学一下女儿家娴静的姿态。
彼时,长宁已有四个多月的身孕,所以尽管阿若不情愿,也不好同一位有孕在身的人闹。故而这禁闭总归还是起了些成效的,阿若确实是安静了下来。
待时间久了,阿若知道这回她父汗是铁了心要整治她,慢慢也愿意同长宁说话了。
长宁话不多,通常是阿若问,她答。阿若也没问她别的,大抵就是一些中原的风俗人情。但长宁自幼养在闺阁,对那些风俗人情也所知不多。阿若问了几回后,便也知趣地拣了些别的东西问。
日子便这般流水似的过,长宁的肚子一日比一日大了起来,转眼白氏便又入了冬。
如今阿若已经习惯每日去长宁帐里转悠一圈儿,瞧瞧她那未出世的弟弟或妹妹。长宁夸阿若是个善心的姑娘,丹溪却对此嗤之以鼻,说阿若的脑子估计是被马踢了。
直到次年正月的时候,长宁分娩,给白氏添了一位小王子,久不露面的父汗这才去长宁的帐篷里坐了坐。也不知他们商议了什么,待父汗走后,长宁叫了阿若进去,塞给了她一封信。
“这封信,劳烦公主替我送到中原。”产后的长宁虚弱至极,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的,但也足够让阿若听明白。她说,“你若思念他,就去见见他。你若不想见他,便替我去瞧瞧,明淮河畔的桃花开没开,可好?”
阿若承了她的后一句话:“我到时候折一枝给你带回来。”但她心里清楚,她真正想做的,其实是长宁前一句话提到的。
她做事讲究有始有终,所以她想见见舒蕴,问一问他,他心里是不是从未有过她。
他若说“是”,她便再不念着他了。
于是报喜的仪仗队顶着白氏凛冽的风与雪,一路翻过涿光山,行至天门,再越过江北天堑,走了大半个月,终于在二月初抵达了中原王都——盛京。
盛京地处江南,冬日里天气也依旧和煦,似乎连风也是软的,吹得裹了狐裘的阿若鼻尖微微沁出了汗。
她被人扶着下马车的时候,前头有人朝她行礼,也不知是不是身体未痊愈的缘故,那人的声音有些沙哑,带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:“恭迎斛律公主。”
嘴角本来扬起了一半的阿若听他这称呼,小脸登时一垮,咬牙愤愤地叫:“舒蕴!”
七
镇国大将军那常年体弱的幼子当街被白氏公主抽了一鞭子的事,很快便传遍了盛京的大街小巷。舒蕴的身子弱归弱,但家世摆在那儿,人生得俊,才情还高,故而仰慕他的姑娘不知凡几。阿若被接进宫后,悄悄给她脸色看的宫女就有七八个,更别提那些说话暗藏机锋,处处在挖苦人的天家贵女了。
毕竟是在别人家的地盘,阿若也不好为了这些不见血的争闹大动干戈。只是她心里到底憋屈,忍了几日后,挑了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翻了皇城的墙,爬了舒家的房。
舒蕴正卧在榻上看书,阿若在房顶闹出了一点儿动静以后,也不见他惊慌,反是吹熄了灯,将书往枕边一搁,叹气道:“下来吧,当心摔着。”
阿若心说真没意思,却还是乖乖地从房顶上下来,翻窗而入。
屋内很黑,阿若摸索着在椅子上坐下后,问:“你熄灯干什么?”
舒蕴倒是耐心,解释道:“这里不比白氏,万一被人看见你半夜进了我的屋子,传出去会污了你的名声。”
阿若撇嘴:“我才不怕。”
说完这句以后,一时又没了话,屋内便安静了下来。虽说阿若后来也能明白舒蕴想回归故土的心情,但她心里到底还是有怨的,故而见舒蕴像是不愿与她多话的样子,便又腾了几分火气上来,手一甩,起身往外走。
身后的人又叹:“公主要往哪儿去?”
“你管不着!”阿若扔下这句话便照原路又翻出去了。
墙外是条长街,这个时辰冷清得紧,只远远听到更夫的梆子声,却见不到任何一个人。阿若一向胆子大,但眼下也不禁怕了起来,蹲在舒家大门前的石狮子下头,偷偷抹起了眼泪。
大老远跑到中原给自己找气受,保不齐她的脑子真被马踢了。
舒家那朱漆大门被“吱呀”一声推开,不多时,一件鹤氅便轻轻披在了阿若身上:“别哭了。”
阿若吸了吸鼻子,只觉得心里酸酸涨涨的。她仰头看着身前显得有些羸弱的男子,委屈地问:“明淮河畔的桃花开了吗?长宁说很美。”
“是很美。”舒蕴在她旁边的石阶上坐下,说,“但明淮河畔的桃花要三月才开。”
阿若揉干眼睛,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,有些失望道:“可我们要不了几日便得回白氏了。”
这还是中原皇室体谅,特准他们多休息几日。毕竟长宁的孩子在二月满月,阿若他们回时轻装简行,脚程快一些,歇几天再动身也能赶上。但中原这边的仪仗因为备了东西送礼,脚程略慢上一些,所以眼下已经动身了。
舒蕴侧首看了看她,像是在思忖什么,好一会儿后才开口道:“公主愿意一辈子留在中原吗?”
阿若怔了怔。舒蕴不等她反应,又接着说道:“你愿意背弃你的族人,离开不句山脉的庇护,从此一辈子囹圄于闺阁,只能得见一寸见方的宅院天地,这样留在中原,你愿意吗?”
屋檐下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晃,暖橘色的灯光幽微,只照得见方寸之地,夜色如浓墨般铺展开,阿若就在舒蕴与平常判若二人的急促问话中顿住了。
她愿意吗?
“你不会愿意的,阿若。即便你如今觉得没有什么,但日后你也会后悔的。”舒蕴替她说出了答案,他第一次这么唤她,语气里处处透着哀伤,“你是白氏的公主,有最自由的灵魂,你在那里出生,也该在那里死去。你死后,陪伴你的是不句山的雪,是草原上的马群和在天空盘旋的鹰,而不是一座孤冷的坟茔,墓碑上连名字都吝啬刻下,只告知后人这是某某之妻。
“趁现在还来得及,阿若,我送你回白氏,好吗?”
八
起先阿若不懂舒蕴说的“还来得及”是什么意思,只以为是舒蕴厌烦她,所以憋着一口气,当即便拒绝了舒蕴的提议,等她明白过来的时候,却已经晚了。
二月上旬,中原的仪仗先行的第五日,阿若一行人准备返程。只是皇城门都没出得去,便被皇家禁卫军围了。
而后阿若被单独关押起来,随行的其他族人生死不知。
当初长宁说中原的皇城里有许多废弃的别院,那里阴暗寒冷,杂草丛生,处处透着绝望,是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,世人称其为冷宫。那时阿若觉得她这话夸张了,心想着,再暗、再冷的地方,也总有阳光能照得进来。但阿若被关押在了这里之后,她便明白长宁的话了。
这种无论怎么大声哭喊,也没有人愿意理你的感觉,的确令人绝望。
阿若喉咙喊哑了,手拍肿了,没力气了,便也就消停了下来,蜷缩在结了蛛网的角落里,数着天黑的次数。等到第二十一天的太阳落下时,除了每日为她送食的老妪,终于出现了别的人。
那人死死抓着她的手,帮她一路躲过了禁卫军的巡视,将她送出了皇城。皇城外等着一匹枣红马,和阿若在白氏时常骑的那匹很像,她翻身上去的时候,还会转头轻轻蹭她,但第三天的时候,它累死了。
阿若没来得及为它哭泣,她用他给的令牌在驿站换了第二匹马,而后没再看它一眼,扬鞭一路过了河西走廊,奔向张掖。
到第六日,阿若从中原骑回来的第三匹马也死了,死在了柴达,和众多战死的马匹的尸体堆在了一起。
和它们堆在一起的,还有数不清的白氏人的尸骸。
她想将他们都埋进土里,可人太多了,她挖不了那么多坑,只能将他们一具具都翻过来,扯下布条盖住他们的脸,不让秃鹫啄食他们的眼睛。
阿若不懂,明明是中原公主的孩子的满月礼,明明她觉得长宁很好,舒蕴也很好,事情最后怎么会变成了这样?
她想起那二十一个日夜中,她某一日听到了围墙外贵女们满含讥讽的话。
贵女说:“舒公子蛰伏数月,同那斛律若假意斡旋,最后拼死一搏,观察到了白氏军队的去向,得知他们每年春初会派出多少人马去寻找新的草场,这才使那借满月礼暗遣我朝精兵的计划得以实施。”
贵女说:“长宁倒也忍辱负重,方去信让她怀孕,她便真掐着点儿怀上了,不过也保不齐是谁的。但总归她立了功,这一回来,身份可就大不一样了,日后再也不用住在冷宫里了吧?说来也可笑,白氏国竟还想用这孩子讨些封赏呢,说什么皇家的血脉,生来尊贵,也不想想,掺了他们的血,那孩子合该下贱。”
丹溪总说中原人都是满口谎言,这话果然没错。
九
天又暗下来,黑云往下压,酝酿着一场大风雪。
阿若不知道翻了多久,其间她翻出了父汗的尸体,翻出了那刚生了女儿的玛雅姐姐,还有一具小小的男婴尸体,她想找到丹溪,但没等她找到,刀上沾了血的中原人便来了。
阿若又被关了起来。这次她被关进了囚车,四周是白氏人一贯用来围牲畜的木栅栏。
他们一路南行,预备沿着当初阿若和她的族人满心欢喜前往中原报信的路,翻过涿光山,行至天门,越过江北天堑。
只是天也似乎在为白氏悲鸣,连着两日风雪不停。第三日依旧如此。有人迎着风雪出现了。
阿若见到舒蕴的时候,并没有太激动的情绪。她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,而后便木然地垂下了头。
舒蕴裹着裘袄,白绒的边儿衬得他眉目越发如画,随意往那儿一立,便是无人敢怠慢的,在白氏灭族的计划中出了大力的舒家公子。
他遣开了守在囚车旁的人,笼在袖子中的手终于伸出来,那里藏着一把锃亮的匕首。
他问:“公主有什么想说的吗?”
阿若想了想,回:“希望下辈子不要再遇到你了。”
舒蕴颔首,将喉中一抹腥甜压下去,轻声道:“好。”
十
《后史》有载:舒家有子蕴,献策破白氏,王师于三月初七得胜回朝,并掳白氏公主。初九,风雪大作,蕴于涿光山迎王师,雪停,公主身死,蕴不知所终。
 2023易稿年度领航人
2023易稿年度领航人 申请成为编辑部成员
申请成为编辑部成员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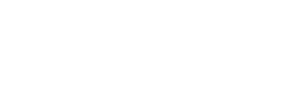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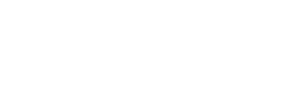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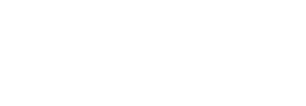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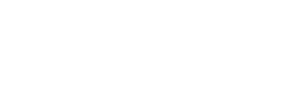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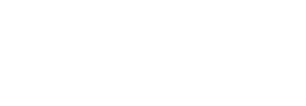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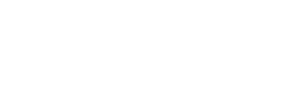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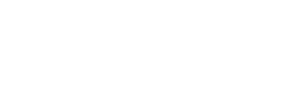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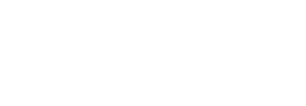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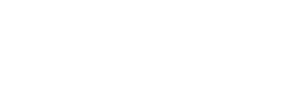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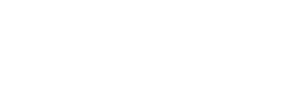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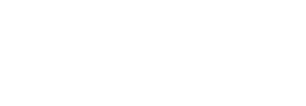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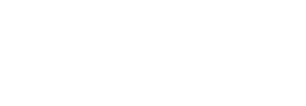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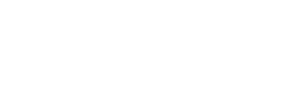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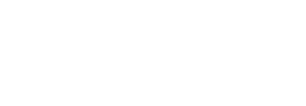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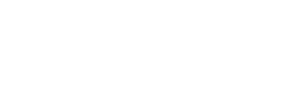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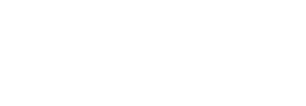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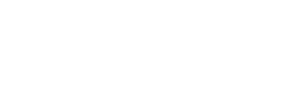

 返回顶部
返回顶部



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18649号
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18649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