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概述:
他始终相信,在那千里之外千年不冻的海港,他的栀妤在等他。
作者/ehcostraw月白
1
尼科巴群岛已经过了,一艘看上去有些年头的中型客运船,准时出现在印度洋。它发黄的船帆并没有撑得展平,只是无精打采地耷拉在桅杆上。
盛夏的海洋,太阳早升迟落,白天闷热,夜晚潮凉。
甲板上的人三三两两,倚着生了铁锈的栏杆闲谈说笑。海的尽头被夕阳染得绯红,一大片云翳托着翻着肚皮的太阳挂在天边将落不落。
在整艘船的末尾,站着一位穿着旧式西装的老人。
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皱纹和斑迹,却没有使他的身子佝偻。
他扶扶眼镜,时不时将胸前的怀表取下擦拭,又时不时望向太阳的方向。
他怀抱着一束很鲜艳的玫瑰,看向玫瑰的时候,像个十来岁的少年郎。目光温柔得仿佛是在看草长莺飞的六月。
这是他在这艘驶向俄罗斯海港的客运船上,看的第六次日落,每天清晨和傍晚他都会出现在甲板上,不说话,只是带一束鲜红的玫瑰站着,等大火球似的太阳升起又落下之后,就整整自己的西装离开。
好像是某种神秘的仪式,简单的动作也被他做的神圣。
几天了,船上的乘客都知道了这个老头儿,一个大夏天还穿西服、一大把年纪扛了一箱子放了玫瑰的冰块上船,每天取三支玫瑰用牛皮纸包好带出去看太阳的怪老头儿。
起风了,甲板上的人群散去,老人对着日落看了最后一眼,也进了房。
这是1987年,许舒雨离开冯栀妤的第五十年。
2
民国二十四年,公元1935年,天津许家花圃开了满园的玫瑰。
次年春,赴美习修音律的天津许家少爷许舒雨,回国成婚。
许舒雨是被父亲为保其平安,强行送去美国的。
他自幼在美国长大,性格孤僻,朋友很少。上音校后更是独来独往,愈发沉默寡言。唯一有联系的,便只有自己的未婚妻,商会主席长女冯栀妤。
他和冯栀妤的故事说来话长。
初遇时,他只当她是笔友,一位远在大洋那岸的精神寄托。
那是五年前的冬天,父亲寄来夹着家书的那本《泰戈尔诗选》。
在那本诗选中,许舒雨第一次“见到了”冯栀妤,那是一种相见恨晚,更像一场久别重逢。
在诗选里,她自称“昨日青”,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书评或注解,但许舒雨依旧能够感知到,她藏在字里行间的不同常人的情怀与格局。
她惯用墨蓝色墨水笔,字生得俊俏,一手簪花小楷。许舒雨用了一个月细细品读完这本诗选,像是和这位“昨日青”相伴走了一程路。
寒山不见昨日青,谁作枝柯晓来冰。
许舒雨欣赏至极。
透过那墨蓝水墨,许舒雨仿佛看见了她。
长发齐肩或短发齐耳,幽幽一帘梦,她是走在窄巷深处的姑娘。举着油纸伞,脚踩着青石砖向前,她的背影是那样漫长,却也是那样的令人着迷。
许舒雨考虑再三,还是给书扉页上的地址寄了信,他说自己唐突,想知道她的姓名。
他本是没抱希望,却意外在两周后收到了回信。
她说无妨,我是冯栀妤,很高兴认识你。
他这才记起与自己已定婚约的冯家小姐,他第一次感激命运。
3
他们成了笔友,或者说是精神伴侣,在两个孤独的年少人心里,所有无法同旁人道出的复杂情愫,终于有了出口。
对音乐痴迷的许舒雨,发现冯栀妤也同样醉心于旋律,只不过他偏爱古典乐,她却为京剧昆曲着迷。
他们同样热爱文学,读新诗,也爱宋词,说歌德普希金,也讲苏轼辛弃疾。
两岸战火焦灼,他们的书信也从音乐聊到家乡,从波佩尔、巴赫聊到民族存亡。两颗年轻的心因音乐和文学相吸,更因共享的精神河流相近。
写信三年,1934年冬,两个早有婚约的年轻人,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像是将整个春天兑进了那年的12月,偷来小熊的蜂蜜掺进日子里。许舒雨与冯栀妤谈起时局时各抒己见,谈起恋爱来蜜里调情。
青春年少,才子佳人,革新抱负,两岸知己。
一年之后,许舒雨与冯栀妤决定完婚,许舒雨回国。
他在海上漂泊七天七夜,终于在1936年的春天,踏上这片陌生的旧土。
他看见飘扬的彩旗,也看见烟尘迷乱的天一望无际。中式阁楼与西洋教堂建筑交错,电线将天空分割成几块。
柏油的公路,成片的梧桐树光秃着树干,黄包车夫休憩在暗巷,未化完的积雪在街角堆积。
天津城的一切都在他眼前展开。
人间烟火,杂乱又热气腾腾。
这就是他的家乡,他许舒雨离别十三年的,魂牵梦萦的故土。
他按照冯栀妤给的地址,找到了一家西式的咖啡厅,他背着大提琴的箱走得缓慢,几乎一步一停。
在他看来,仿佛是十多年的风景一同塞进眼里,他渴望旧物的填充,却也渴望新鲜的空气。
他深吸一口气,推开咖啡厅的大门,不礼貌地四处寻望,摆手阻止了上前的服务员。
忽然,他看到一个身影。
是她吗?
4
许舒雨在厅内左手边的第三个位置上,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梦中背影重合的年轻女子。
穿一件月白织锦旗袍,外系浅青哔叽斗篷,上绣银线兰草,齐肩长发如清泉而下,清雅幽静,明眸皓齿,眉目如画。
“你好,我……”许舒雨走上前去,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“你是许舒雨吧,我是冯栀妤,你的未婚妻。”年轻女子笑语盈盈,暗香来去,许舒雨站的有些近,嗅到女子衣摆的淡香,如同那簪花小楷,亦如这月白衣衫,沁人心脾,和初雪一般纯净。
那是他第一次见她面,却好像早已见过千万次,在信里,在梦里,在心里。
一局尽欢,落日将至,冯栀妤提议:“要不要去海边走走?”
“好。”许舒雨回道。
那天日落得很早,坐在海边的台阶上,码头工人在橘色的余晖中忙碌。海并不好看,只是广阔,广阔得让人心慌。
“栀妤啊。”他第一次这样叫她。
“嗯?”
“你想要一场什么样的婚礼?”许舒雨刚问出口就想缝上自己的嘴,虽然已经谈了三年恋爱,但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对方婚礼的?他在心里骂自己嘴笨。
“没有想过,但我还是喜欢老式的嫁衣,学校的同事们都说西方的白纱漂亮,我倒是欣赏不来……
只是,我看着西洋婚礼上的玫瑰红得好看,仿佛是在讲“‘啊,这是多么热烈的爱啊’,多有趣!”冯栀妤倒是毫不避讳地絮絮叨叨讲了不少,边讲边用手绕着自己披风上的抽带玩。
“你喜欢红玫瑰?”
“算不上喜欢,只是觉得这红玫瑰开得灿烂浪漫。就像你看那夕阳火红,是海与天在为太阳贺礼。
“每日两次,迎来送往,用的都是鲜艳的红,这是天地的心意,人是该起立行注目礼的……我呢,就只盼此生像花,哪怕盛放一瞬就枯萎,入风入泥,也算不枉花生。
“哎说起花生,我倒是想吃花生了,我们过会儿可以去徐家铺子买点干果吃。”
“花生?哈哈哈,怎么办?聊到现在我才敢认,你是和我跨国写信的昨日青。栀妤啊,你放心,等到我们结婚那天,我定会带着三支火红玫瑰走向你。”
他与她相视一笑,继续并肩看海。
波浪将夜幕深深掩埋,有情人在星光下偷偷动心。
5
一周后,许舒雨约冯栀妤城西放鱼灯。
小鱼灯随处都可以买到,许舒雨只是领着冯栀妤进了一件小作坊里,说我们自己做。
裁纸固杆,研墨作画,他们像是一对生活许久的寻常夫妻。冯栀妤画了两只白兔,又在边框上涂上花纹,而许舒雨在空白处提字。
冯栀妤拿着自己的作品,颇为满意地点头。
他们随着人群走到河边,在鱼灯肚子里点上一只细蜡,放置水中,冯栀妤双手合十,念念自语。
“你许的什么愿?”许舒雨第一次放鱼灯,看得新奇。
“不告诉你,你也快点许一个吧,船都要飘走了。”
“那我许愿,冯小姐的愿望都成真。”
“我不后悔遇见你。”冯栀妤望向许舒雨的眼说到,只见后者目光里满是柔情。
他们坐在河岸说起婚事,许舒雨说父亲南下商谈,可能下半年才会回津,婚事可能会迟一些。
冯栀妤说没关系,哥哥还在俄港摩尔曼斯克运水货,几年了都不曾见过。
“摩尔曼斯克?可是那座千年不冻港?”许舒雨转头问到。
“是啊,据说好像是因为那里的暖风。”
“小傻瓜,那是因为大西洋暖流的到来,使摩尔曼斯克千年不冻。就如同春风之于花朵,你之于我。我因为你的到来,所有的寒冬都过成暖意。”
许舒雨看向冯栀妤,远处烟火绽放,人头攒动。但他的眼里只有她,他的昨日青,他的冯小姐,他的未婚之妻。
6
第二日,许舒雨差人送去冯栀妤爱吃的桂花糖和玫瑰糕。
第三日,冯栀妤送来珍藏的诗集和昆曲戏本,上面依旧是墨蓝的批注,像是送来了一段时间与一段情意。
半年后,许禄知商谈结束,自金陵返津。许冯两家约了时间见面吃饭,商定婚事。
许舒雨陪着冯栀妤挑婚服,写请柬,订饭店。
他许诺他会给她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,他要她做他最美的新娘,他要让全天下所有未出阁的姑娘小姐都羡慕她。
她笑着打他,说我要这羡慕什么用,只愿人长久,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。
冯栀妤后来回忆说,那是她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,觉得幸福离自己触手可及。
许舒雨选了一束鲜红的玫瑰,是他半年前回天津之后种的,好不容易开花,他想将这一束最美的花,送给他心上最美的人。
订婚典礼上,许舒雨说:“如今心灵已开始苏醒,这时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你,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,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。
“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,为了它,一切又重新苏醒,有了倾心的人,有了诗的灵感,有了生命,有了眼泪,也有了爱情。”
是那本《普希金诗选》里《致凯恩》的诗句,是他们的开始。
“定不负君意。”冯栀妤最后讲。
在一片祝福与欢呼声中,许舒雨亲吻了冯栀妤。
那月天津城内所有的报纸头条,都刊登富甲一方许禄知三子许舒雨,与商会主席冯进麟长女冯栀妤即将成婚的消息,强强联姻,郎才女貌,羡煞众人,一时风光无量。
7
像是突然断了线的风筝,天也不遂人愿。
大婚前一个月,七月二十九,天灾人祸,天津沦陷。
一切都成光影泡沫,和那天酒店顶上的水晶吊灯一起,砸向地面。
往日繁花似锦的天津城人心惶惶,有钱有势的大家世族纷纷出国避难,大火连天,战火纷繁。
冯家联系好了船只,欲前往俄港摩尔曼斯克,出发前一天晚上,冯栀妤约许舒雨出来商议一同赴俄之事。
他说没有问题,明天早晨十点,他会和她一同前往俄港。
第二日,他在汽笛响起的前一刻慌乱地跑下船,消失在人群里。
刚去取完早餐回到房门前的她,愣在原地,骨子里渗着寒意。她发疯似的四处奔跑寻找都没有结果,最后在衣兜里发现了他留给她的信。
他说,栀妤啊,我曾想在这片土地上,留下自己的一滴相思泪、一段儿女情,但如今我也想在这片土地上,留下自己最后一滴少年血。
他说,吾辈生正逢时,儿郎之命,自当献于民族国家。
他说,栀妤啊,我对不起你,如果这次有幸避过这一难,待天下太平,我一定会去找你。你要好好活着,像玫瑰一样鲜艳,像太阳一样长久。
冯栀妤捧着信站在风中,泪被风吹干。
她何尝不懂他的抱负与情义。只是他为什么不早告诉她?为什么?
她无声地哭泣,不停地说好,说我愿意,我会在摩尔曼斯克等你,一直等你。
这句本会在婚礼上说出的愿意,现在竟成了她亲手将自己挚爱推离的话语。
汽笛长鸣,没有退路。
8
旧梦已醒,许舒雨从竹椅上坐起。
那年一别,他一个转身,就与她生离。
他参加了革命,在枪林弹雨里辗转多地,很幸运地活到了战争结束后。他到了南方,做了点小生意。
只是他不再碰音乐,因为他知道大提琴旁,不会再有人软声细语地唱昆曲。
今天是他第十三次去摩尔曼斯克,前十二次都未曾见到她。此次前去,是朋友说有新的消息,无论真假,他都要去试一试。
他始终相信,在那千里之外千年不冻的海港,他的栀妤在等他。
这些年来,他无数次祈求自己的思念会化为港上一缕暖风,代替他将她拥在怀里。因为他爱她,而爱永不过时,哪怕跨越的是山海和世纪。
许舒雨穿着那年为婚礼定做的旧式西装,虽时隔经年却依旧平整如新。
他戴上插花礼帽,看上去好笑又滑稽,但他并不在乎,依旧目光柔和地看日升日落,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她所说的对太阳的贺礼。
他第十三次登上了那艘当初没有登上的船,拿着约定好的三只玫瑰,去赴一场迟到五十年的旧约。
他不知道自己此行是去求婚还是祭奠,但他依旧决定要去,因为毕竟摩尔曼斯克的海风,已经为他吹拂了半个世纪。
飞鸟划过天空,汽笛声再次响起,客运船缓缓靠岸。岸边站着一位老妇人,虽韶华已逝,但风韵犹存。
海风轻轻吹着,许舒雨沿扶梯走到地面站定。他什么都没说,只是温柔地注视着她,一如往昔。
作者介绍:ehcostraw月白。当蓝色的夜坠落在这世界时,没人看见我们手牵着手。
卿久寄语:再次看到ehcostraw月白的文章,笔触依旧温柔细腻,又向我们展示了一场长达五十年的爱与被爱!
 2023易稿年度领航人
2023易稿年度领航人 申请成为编辑部成员
申请成为编辑部成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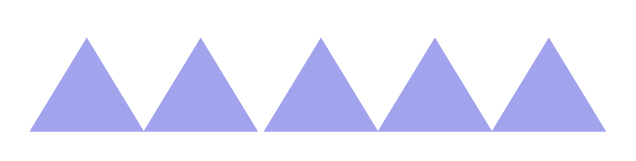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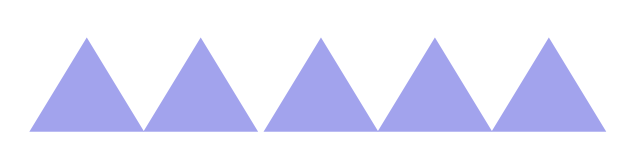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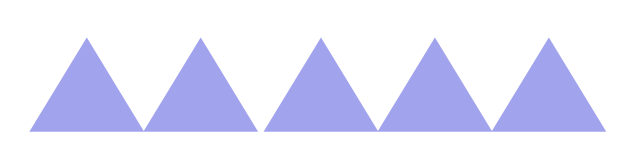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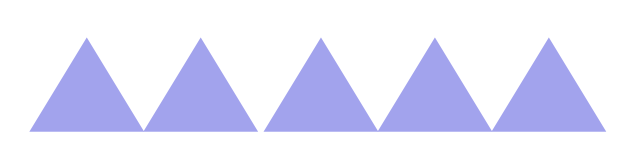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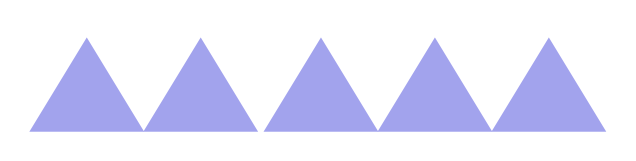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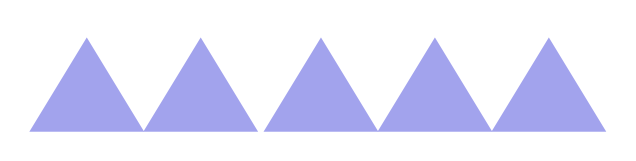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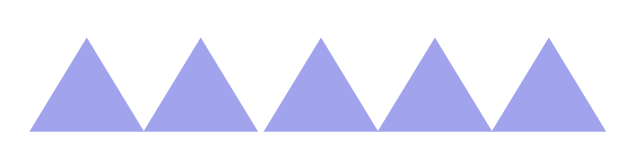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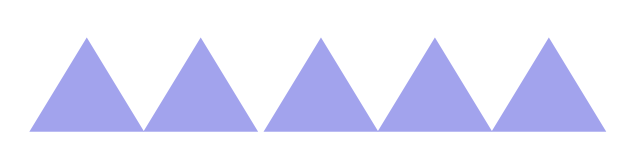

 返回顶部
返回顶部



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18649号
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18649号